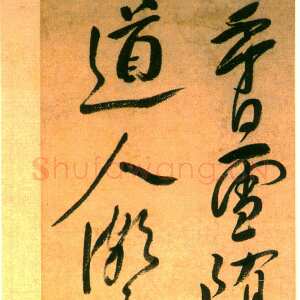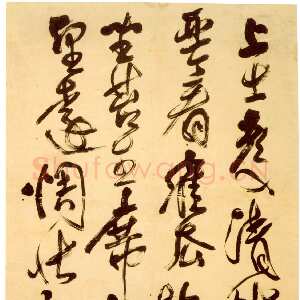名称:阮元与浙派印人交游考
书法家:阮元
分类:书法文摘
备注说明:书法百科知识
琅嬛仙人是指阮元,因为阮氏有斋号琅嬛仙馆。此诗既可看出陈鸿寿对其学师阮元的仰慕之情,诗中所表露的“大书深刻”、“气体深厚”,又明显看出受其师碑学思想的影响。他的书法、篆刻创作在以阮元为首营造的金石书画文化圈中受到滋养和启示,他在书法篆刻艺术上的成就不能说与这样一个文化圈无关。
阮元在任浙江学政期间,乘輶轩采风,足迹遍十一郡,或访诸耆宿,或询之多士,各出所藏,随收随录,编辑《两浙輶轩录》。《两浙輶轩录》收录了清初、中期浙人诗三千馀家,此间,参与采访校订者人数不少,邵志纯、朱朗斋、吴澹川、李香子、郭频伽等,当然也少不了陈鸿寿、陈文述兄弟,阮元在《两浙輶轩录》凡例中说:“钱塘陈曼生(鸿寿)、陈云伯(文述)……亦于京邸校阅一过,多所订正。”嘉庆三年(1798)书稿成,没有及时刊刻,存于官邸。嘉庆六年(1801)夏六月,阮元在朱朗斋、陈鸿寿的请求下,遂将书稿交于他们二人刊刻,也就有了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两浙輶轩录》朱朗斋碧溪草堂、陈鸿寿种榆仙馆同刊本(图一)。
嘉庆九年(1804),阮元为陈鸿寿的《种榆仙馆图》题诗一首。后又为其《种榆仙馆三图》作记,阮亨说:“陈曼生于画精鉴别,……最喜奚铁生画,尝以其晚年作,偕方兰坻、王椒畦合为一卷,家兄为作《种榆仙馆三图记》,论画、论人,兼以记传之法。”
阮元所用印章多出陈鸿寿之手,这在他的从弟阮充的《云庄印话》中找到一些证明,阮充说:
文达公归田后,序林茮生鸿《小碧琅玕馆印谱》云:余童年用印倩毕,旋之刻一小田黄“阮元印”,携入京师,随用六十年,不胜平漫,直至癸卯毁于火。次则门生陈曼生在余幕刻者最多,曼生与表弟林小溪同幕同朝夕,宜乎其多得曼石矣,曼生石一时推重,时奚铁生、王椒畦之画又同重一时,林氏梅花屋画卷在表侄处,故茮生专法曼生,曼生为余刻“阮氏琅嬛仙馆收藏印”,今只此一印存矣。
从《沈周野翁庄图卷》中我们能见到一方不太清晰的“阮氏琅嬛仙馆收藏印”(图二),从内容和风格判断当就是这一方。从陈鸿寿所留印拓中还能寻到“琅嬛仙馆鉴定”(图三)、“扬州阮氏琅嬛仙馆藏书印”(图四)等印章,阮元又说“盖尔时有印皆出曼手”,可见陈鸿寿在阮元幕府中刻印不少,也为阮元刻印不少,由此可见阮元十分喜欢陈鸿寿的印章,他所结交的篆刻家很多,而偏喜欢用陈鸿寿所刻。一方面,陈鸿寿经常在其身边,在金石、书画方面受阮元影响较深,审美观的接近是很自然的事情,另一方面,表现出阮元对浙派印风的偏爱。阮元所用印章多为浙派,有些虽不知作者(图五),从风格上来看可能也是陈鸿寿所刻,但属浙派风格无疑。
四 阮元与其他浙派印人
西泠八家中,还有两位印人与阮元有着良好的关系,且属于阮元金石文化圈中的人物,一位是陈豫钟,一位是赵之琛。
陈豫钟(1762—1806),字浚仪,号秋堂,浙江杭州人。深于小学,好金石文字,收藏甚丰。篆刻服膺丁敬,又崇尚汉印,有自己的风格。著有《求是斋集》。
阮元小陈豫钟2岁,为同辈人,但陈豫钟和陈鸿寿一样,都视阮元为师。陈豫钟刻有一方白文印“琅嬛弟子”,(图六)可见他视阮元为师,对阮元的景仰之情由此表露出来。以阮元为首的乾嘉学派提倡实事求是学风,“实事求是”一词此时极为流行,陈豫钟的斋号求是斋就是受此影响而取的。
嘉庆七年(1802),阮元在浙江为文庙制乐器,复铸镈钟,命陈豫钟为其铭摹写古文,铸成后,阮元叹赏不止,招之不往。阮元重新编刻《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嘱陈豫钟摹写款识,阮元在《定香亭笔谈》卷四中说:“钱塘吴寿朋(文健)明于小学,审定文字以付梓人;陈秋堂(豫钟)精篆刻,为摹款识;高爽泉(垲)善书,为录释跋,皆一时之能事也。”
阮元这样评价陈豫钟:
钱塘陈秋堂(豫钟)深于小学,篆隶皆得古法,摹印尤精,与曼生齐名。秋堂专宗丁龙泓,兼及秦汉;曼生则专宗秦汉,旁及龙泓,皆不苟作者也。曼生工古文,善书画,诗又其馀事矣。
而西泠八家的另一印人赵之琛(1781—1852)与阮元的交往见于文字的不多,阮元长赵之琛17岁,阮元在编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时,其中的古器文字多半由赵之琛手摹。阮元与陈豫钟、赵之琛的交往也多半属于金石之交。
浙派印人与阮元有交游者,除了西泠八家中的黄易、奚冈、陈鸿寿、陈豫钟、赵之琛五家以外,与之关系密切的还有屠倬。
屠倬(1781—1828),字孟昭,号琴隖,晚号潜园,浙江杭州人。嘉道年间著名学者,能诗擅画,其篆刻名盛当时,属于浙派,篆法、刀法专学陈鸿寿,刻款用丁敬法。
屠倬是阮元的门生,阮元长其17岁。他们的相识应当很早,这从阮元的诗句“我早识屠君”中可以得知。嘉庆十五年(1810),阮元在屠倬任仪征县令时有长诗送行,题为《门生屠琴隖倬以翰林改宰仪征,翁覃溪先生倡咏饯送,遂亦以诗赠行》,节选如下:
展我泰华碑,洗我八砖研。
别斋倡和篇,旧友共相饯。
屠君正壮年,出宰我乡县。
乡县尚不陋,长江绕芳甸。
近者集盐艘,民风少为变。
枭徒颍泗来,小斗竟如战。
我昔谋增兵,请者议未善。
为此多隐忧,保障匪易见。
我早识屠君,恍恍吴越彦。
清名满湖海,高文冠翰院。
百里非宠才,帝欲使之练。
孰意赤紧州,巧得颜谢选。
……
屠倬上任的仪征恰是阮元的籍贯地,故阮元有“出宰我乡县”之语。屠倬在阮元的泰华双碑之馆欣赏到《泰山刻石》和《华山庙碑》以及晋砖等古碑石刻的拓片,当对其金石方面的研究有所帮助。阮元此前又有《屠琴隖庶常倬将出为县令,所寓京城米市胡同有古藤二株,自绘图卷索题》、《题小檀栾室读书图三首》等诗多首,阮元手书有《为屠琴隝行书杂诗卷》等。屠倬也有多首诗赠阮元,《是程堂集》中就收有《题画杂体呈大中丞阮云台先生》、《大中丞阮云台建白文公祠于孤山之左,以五月八日落成,同人酹酒祠下即席呈中丞》等。阮元和学者的交往虽多是建立在经学上的,但与金石、书法、篆刻、绘画无不涉及,他的思想常对人们产生很大影响,阮元也将他收藏的《西岳华山庙碑》四明本给屠倬欣赏,屠倬有诗《集苏米斋覃溪先生出示手摹华山庙碑凡三本,云台先生复出新刻四明本相较,赋呈两先生》见证,诗中有句:“四明旧拓更完好,原本新弆琅嬛仙。譬如真形现全岳,不缺不烂曾夸全。”对阮藏四明本的完好表示出赞叹,从两人的诗中可见他们的交谊之深。
嘉道年间的浙派印人身在乾嘉学派最后的辉煌时期,金石考据学风靡一时,访碑、赏碑、研碑之风盛行,对钟鼎彝器、古碑断碣刻意搜求。阮元适时而起,提倡碑学,于是本来就已见苗头的碑派书法藉着他的理论迅速蔓延,得以在二王传统帖学之外开辟了另一途径。实际上,对当时篆刻艺术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称篆刻中的浙派为书法中的碑派,他们何止是时间段上的一致,所运用的手法、追求的意境也是那么相似,是乾嘉学派背景下的一对双胞胎。乾隆年间的丁敬“仿汉刻烂铜印”就是强化“金石气”的表现,此后的七家更在篆刻中着重于刀的表现,刻意追求笔画的斑剥效果,浙派用刀的“短刀碎切”一如碑派书法用笔的“积点成线”,这与书法家追求苍茫的金石气是一致的。实际上,浙派印人标榜仿汉,已与赵孟頫所提倡的汉印有着本质区别,他们虽在篆法和结字上承袭汉人,但刀法所表现出来的意韵已与汉人有别,已从汉印的质朴走向苍茫,白文印如此,朱文印也如此,已不同于元明印的雅逸流美,而呈现出沧桑的凝重。所以阮元喜欢浙派印章是情理之中的,这与他的观念相吻合,与翁方纲一样,阮元对印章的观点属于“质厚说”,他在浙派印章的发展过程中对印人有一些观念上的影响当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