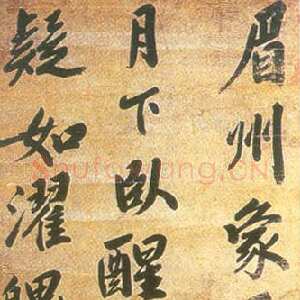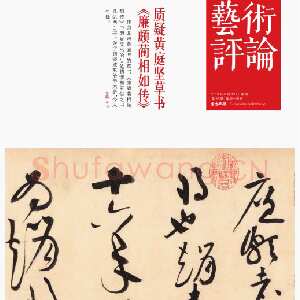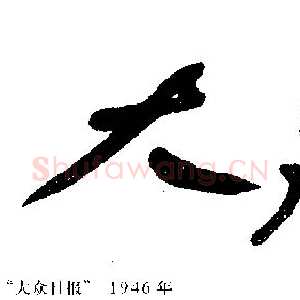名称:牵罗补屋思偏逸,织锦成文意自如——浅析黄媛介文学作品(作者:郑 珺)
分类:书法文摘
备注说明:书法百科知识
一
黄媛介字皆令,明末清初浙江嘉兴人。文学黄象三(有作象山)妹,黄葵阳族女。与姊媛贞(字皆德)俱擅丽才,而媛介尤有声于香奁间。沈宜修辑当时女子才甚者十八人之作为集,名《伊人思》,媛介为作者之一。媛介本儒家女,性情淑警,髫龄即娴翰墨,好吟咏,工书画,以诗文出名,人以卫夫人目之,为世所称赏。早年许杨世功,世功家贫萧然寒素,然皆令终归之,与其黾勉同心,恬然亦自乐也。后乙酉鼎革,家被蹂躏,夫妇协游江湖,交游颇广。垂老会石吏部有女知书,自京邸遗书币强致为女师,舟抵天津,一子溺死,明年女又夭,遂无子,懑甚南归。过仁宁,佟夫人贤而文,留养疴于僻园,半岁卒。
媛介一生,创作颇丰,著有《南华馆古文诗集》、《越游草》、《湖上草》、《如石阁漫草》、《离隐词》。顺治十五年,皆令与梅市胡夫人、祁修嫣等唱和得《梅市唱和诗钞》,有毛西河作跋。然,以上诗集皆已佚失,现存《黄媛介辑本》为后世所辑,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所载:“今从《然脂集》辑得二十五首(《越游草》十五首,《湖上草》六首,《扶抡续集》一首),《诗源》一首,《诗媛十名家撰》二首),《撷芳集》九首,《彤奁续些(上)》二十首,《梅村诗话》八首,《柳絮集》七首,《两浙輶轩录》二首,共七十一首,录成一卷。”
黄媛介生活在明末清初,这是一个改朝易代的国变时期,连年的战乱,流离失所,使知识分子和广大的老百姓一样深受“身阅鼎革”带来的侵害。尤其是对股栗于董狐之笔,它年青史的传统士大夫来说,流芳千古还是遗臭万年,也许就在何去何从的一念之间。与媛介交好的吴伟业和钱牧斋就面临这样的抉择:在顺天从命的通达之下,将道德信守屈从于生命意识来顺从新的统治力量是办不到的。那么,或则以殉节去实践道德信守,通过肉体的毁灭以获得灵的绝对超越;或则削发为僧,皈依佛门,过一种活着的“殉节”生活;或则遁迹山林,退守田园,求得道德与生命的形式的兼取。吴、钱都选择了最后一种,但这种选择本身就包含了退与进的两重性,仕而隐,隐而仕不过是一道门槛的差别。在新王朝建立初期需要巩固统治的特定环境下,特别是民族间的隔膜对立,个人的抗拒无疑将危及生命的存在,而作为前朝旧臣,吴、钱有着才高名大的地位,理所当然要成新政权注目的对象。自古忠孝难两全,为了保全家人,他们被迫出仕,最终逃不掉清廷的征辟而煎受着为“贰臣”的巨大痛苦。
与此同时,作为官眷的一批名媛们也踯躅于自心爱国,归于前朝而夫君却为“贰臣”的矛盾中,苦不堪言。比如钱牧斋的侧室河东君柳如是,比如曾被陈维崧《妇人集》评为“南宋以来,闺房之秀,一人而已”的徐灿。柳如是曾在乙酉五月之变后,劝夫婿就义赴死,然“宗伯(钱牧斋)谢不能” 1(《柳如是事辑》上编卷一)于是如是欲奋身于自家后园的池塘中独殉国难,却被丈夫拽住,而不得。后世因此称其为“凛凛有丈夫风” 2(罗振玉《负松老人外集》)。徐灿的丈夫陈之遴以明朝进士,出仕新朝弘文馆大学士,而徐灿身罹故国沦亡。爱者故国,所依者夫君,面临旧朝的半壁河山也不复存在的现实,国忘而丈夫竟仕!在忍受故国沦丧的同时,又增添了一份莫大的屈辱。这是有别于吴、钱等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形式的灵与肉的分割。这种双重的痛苦使得徐灿的心灵孤寂,无所依傍,而心生 “故国茫茫,扁舟何许”的感叹。
名士如许,名媛如许,在这个非常时期,文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都面临着巨大的考验,他们饱受战乱的创伤与精神折磨的双重苦难,作为乱离中的一介弱女,媛介亦未能幸免。她“产自清门” 3,儒士之家,乱世更显清贫,其姊媛贞迫于家境,远嫁贵阳,为当时贵阳太守朱茂时继妻。而媛介的未婚夫杨世功纳聘后,家中一贫如洗,无力娶亲,后世功又流落苏州,久客不归。期间,有名人豪客登门说亲,愿以千金聘娶媛介。而媛介不改初衷,一片痴心待得落魄浪子他乡归来,与其樆结。成婚后不久便遭鼎革之乱,“乃跋涉于吴越间,困于槜李,踬于云间,栖于寒山。” 4好不容易安定下来,又被人强为女师,于是又“羁旅建康,转徙金沙,留涉云阳。” 5途中舟抵天津,儿子溺水而亡,第二年女儿又不幸夭折,真可谓家破人亡!因此媛介所作多“流离悲戚之辞”,但去温柔敦厚,怨而不怒,足观其人格的纯真。无怪乎姜绍书在其《无声诗史》中成其“此闺阁而有林下之风也”。
二
1.对广大民众的关照
文学作品是作者对现实生活的审美认识。明末先是李自成起义,再是清军入关,崇祯皇帝悬身毙命。连年的战乱与流徙固然使黄媛介羁縻煎迫,潦倒浮生,然而,无论是在流徙途中的亲身经历,还是所见所闻,都丰富了她的写作材料,从而使她的文学作品开掘出比以往的闺阁之作更为广阔的投注对象。继之使她的文学作品体现出国变时期的闺阁诗人独到的气质而与以往的闺阁之作大相径庭。
在风雨突变的多事之秋,长年的辗转使人饱经颠沛之苦,作为一个有着独立人格且不慕权贵的女性,黄媛介亦难免产生凄惶之感。这种凄惶之感缘于她对国家和民众的深重忧虑,缘于她对摇摇欲坠的明王朝迷惘矛盾而又有所希冀的心情。她的《长相思·春暮》就是由这种心绪凝铸而成的:
风满楼,雨满楼。风雨年年无了休,余香冷似秋。
卖花声,卖花舟。万紫千红总是愁,春流难断头。
这首双调小令又名《双红豆》,前后各三平韵。一般人都将此词定位成一首愁妇遣怀之作,但若考察过黄媛介的身世和她所处的时代,那么就不难发现这首词与一般的愁妇抒怀之作是有很大的差异的。上片首句“风满楼,雨满楼。”化用了唐代许浑的《咸阳城东楼》中的诗句“山雨欲来风满楼”而成。形象地描绘出明朝大势已去,形将就末的形势,也流露出对此无可奈何的哀叹。“风雨年年无了休”和“余香冷似秋”是作者由动荡的时代联想到自己这个生在不幸年代里的弱女子,在为生计的奔波中过早地逝去了青春,剩下的岁月如同风里落花,不知能几何时。残命如同冷秋,一种悲怆之感摧己心碎,这是历史背景造成媛介这般的心态,是于时代之不幸抒写身世之感。下片由上片的虚写转为实写,“卖花声,卖花舟”这是作者由于叫卖花声传来而吃惊,看见载满繁花的小船,百花争妍,何等热闹。在旁人定会惊喜而赞叹一番,但此时的媛介已是一个识尽沧桑,心系国忧的人,在她眼里没有朱熹《春日》诗中的“万紫千红总是春”的喜悦,有的只是“余香冷似秋”的感伤和内心怨愁的具体吐露。用一个“愁”字来点化此句,如果没有切肤之痛怕是难得此句,作者可谓用心良苦。但她并未就此戛然而止,而是更进一层,“春流难断头”,此愁此忧如一江春水,无休无止。由此可见词人忧虑之深了。
另一首《丙戌清明》诗亦体现了她怀恋故国的情怀。从题名上看,写作此诗已是清世祖顺治三年了,但作为前朝“遗民”媛介仍耿耿于怀。每逢佳节倍思亲,何况明室新亡,父母离散,正值清明漆室之忧与白云亲舍之思,纷纷向诗人心头袭来。她写道:
倚柱空怀漆室忧,人家依旧有红楼。
思将细雨应同发,泪与飞花总不收。
折柳已成新伏腊,禁烟原是古春秋。
白云亲舍常凝望,一寸心当万斛愁。
首句的“漆室”是春秋时鲁国的一个邑名。鲁穆公年老太子幼,国事颠危。漆室一少女深以为忧,倚柱悲歌。后来就用“漆室忧”作关心国事的典故。一个“空”字又自我否定了“忧”的意义。一方面自叹无力扭转江山易主的的客观现实;又启下:表示自己对那些与社稷倾亡无动于衷、依旧红楼歌舞尽情享乐的豪门贵族的愤懑。颔联用“将”和“与”把情和景糅合在一联诗中。“细雨”、“飞花”是清明的景致又是抒写羁愁、慨叹韶光易逝的传统意象。宋代词人秦观的《浣溪沙》(漠漠轻寒)中就有“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将“飞花”和“细雨”连用,表现了一种绵长无尽、浸渍一切的惆怅心情。但这里黄媛介没有用“似”、“如”之类的表示明喻的字,而用“将”、“与”等连词把无形的“思”和有形的“泪”直接与景“细雨”、“飞花”联系起来,并缀以“应同发”、“总不收”,明确地指示出此情因此景而生的密切关系。晚唐诗人罗隐《魏城逢故人》中也有类似的构句:“上将别恨和心断,水带离声入梦流。”两相比较,罗诗含蕴更丰,情景糅合更自然,而此诗就有些过于质实、显露了。颈联以古、新相对。折柳:古人临别,有折柳相赠的习惯;伏腊:夏为伏,冬为腊,这里指代岁月。诗人自辞别故乡、亲人以来,岁月更替。而寒食禁火,却还沿袭着古来的习俗。“折柳”、“禁烟”还保留着古代的风习,而江山易代,已不似当年,清明节的景物、风情,无不触发诗人的今昔盛衰之慨。尾联前一句描状。“白云亲舍”:唐代狄仁杰到并州去做官,他的父母还住在河阳。赴任途中,他登太行,南望白云孤飞,说:“吾亲所居,近此云下!”以后就用它为思亲的典故。诗人常常凝望白云飘飞。“寸心”涵载着沉重的愁思。寸心:微薄之心。唐代诗人孟郊《游子吟》有:“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里既用成典写游子思亲之心,又以“寸心”和“万斛愁”对比,极言忧愁深重得令人难以承受,显然,这里包含着比思亲还要深远的“漆室之忧”。
黄媛介的忧国忧民之心还体现在她对穷苦人民的深切同情。身为煎受国难中的一员,媛介对人民颠沛流离的生活苦痛有着深刻的切身体验。乙酉遭乱后,皆令一直过着一种羁旅生活。王端淑尝以诗云:“买舠急欲探先春,风雪偏羁病里身。闻有梅花供色笑,客途如尔未全贫。冻笔涂残半是鸦,剡溪渺渺竟迷槎。相逢只恐梅花笑,怪我年来不忆家。” 6读此诗可以想见媛介的身世了。然而就是在这种病苦穷愁的境地中,皆令亦怀存济民之心,她在一首五绝诗中云:
倾橐无锱铢,搜瓶无斗升;
相逢患难人,何能解相救?
《玉镜阳秋》中评此诗说:媛介“家无儋石,而心存济物,襟情不凡。”她的另一首五绝云:
一日饥寒见,三年感愧深;
君看水流处,一折一回心。
被《玉镜阳秋》评为:“困心衡虑之言,殊有学问之气。”时人亦有评媛介“德胜于貌”,与其交好的吴梅村(吴伟业)认为“此言最为雅正”7由是而见媛介之厚德矣。
2.对自己生活情态的关照
拍合时代历史的黄钟大吕之音固应成为倾注的焦点,空谷幽兰的馨香也独具风韵。作为一个女子黄媛介亦有女人特有的细腻直觉,她凭着这一份直感来观照自己的生活情态,使她的作品题材除了反映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外,相对地集中在对自己生活情态的表现上,如上述所引的两首五绝亦是她奔波于江浙之间时困顿生活的真实写照。另一首《夏日纪贫》是僦居杭州时,贫苦生活的实录。诗云:
池塘水涨荇如烟,燕啄萍丝翠影悬;
高壁阴多能蔽日,新荷叶小未成莲。
著书不费居山事,沽酒恒消卖画钱;
贫况不堪门外见,依依槐柳绿遮天。
前四句写居处之景,描绘江南秀丽的景色。首二句言春水涨池,荇菜茂密,绿荫一片,池塘岸边翠柳低悬,柳姿倒映于含敛的水面,燕子误啄水面柳丝的倒影,错把翠柳当绿萍。以燕子的错觉衬托柳池之美,艺术想象甚丰,艺术效果甚佳。颔联两句写门前清幽的环境,物象赏心悦目。后四句写生活的贫况。据《两浙輶轩录》记载:黄媛介“乙酉遭乱,徙吴阊,羁白下,后入金沙,闭迹墙东,张无放及夫人于氏资给之,时时往来虞山与柳夫人为文字交。其兄开平不善也。然皆令实贫甚,时鬻诗画以自给,后僦居西陵。所居一楼与两高峰相对,隃糜侧理,是其经营终不免卖珠补屋之叹。”诗末两句言贫困难堪至羞于出门见人的地步,只好幽居一隅,而门外柳槐依依多情,以绿荫遮天蔽门,正好帮助她闭门自守,谢绝人事。
宋瑞芝《中国妇女文化通览》称:“中国妇女的非人生活到了明清两代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阶段……女子在娘家是没有财产继承权的,妇女只能分得一点嫁资。出嫁后,即使娘家陪嫁的产物,在名义上也不属于个人,而归属于丈夫。”从中可以见出明清时期妇女经济地位的底下。然则媛介却能“以轻航载笔格,诣吴越间。……赁一小阁卖画自活” 8实属不易。她在《离隐歌序》中是这样评价这段生活的:“虽衣食取资于翰墨,而声影未出于衡门。古有朝隐、市隐、渔隐、樵隐,予迨以离索之怀成其肥遁之志焉。”身处潦倒之境而志不消沉,这种达观的人生态度在一个女子身上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媛介与吴梅村为文字交,两人时相唱和。她曾和吴梅村诗四首,皆是对自己当时生活的描写,体现出一份耽于清贫的闲淡自然。其中第三首写道:
石移山去草堂虚,漫理琴尊葺故居;
闲教痴儿频护竹,惊闻长者独回车。
牵萝补屋思偏逸,织锦成文意自如;
独怪幽怀人不识,目空禹穴旧藏书。
情感生于人生的波折动荡,对黄媛介来说,几经战乱后,还能有“闲教痴儿频护竹,惊闻长者独回车”的闲情逸致,这种大动之后的淡定尤显得来之不易。所以就算是面对“牵萝补屋”的窘境也依然可以抱以一种“思偏逸”的乐观心态了。由此可见,黄媛介是一位冰清玉洁、胸襟不凡的女诗人。在价值观念以“女子无才便是德”为时尚的时代,“才思非妇人事,华藻乖福寿之征” 9,更兼出身清寒的女子,要在文学这块集中凝结体现着汉文化精蕴的苑囿内竞秀于众芳,实属非易。黄媛介没有丝毫的懦弱自卑,“独怪幽怀人不识,目空禹穴旧藏书。”发自才华与心性的自信更付诸于勤奋,印证以成就,终于诗名噪甚。
黄媛介不但工诗,而且善画。诗学杜少陵,画学元代画家吴镇。吴镇认为作画不一定要师法自然。黄媛介的一首题画诗《题山水小幅》就抒发了自己这方面的一些感受。诗是这么写的:
懒登高阁望青山,愧我来年学闭关;
淡墨遥传缥缈意,孤峰只在有无间。
诗的头两句写作“力入笔研”,以求有得于心的情形。在闺中,苦闷寂寥,登上高楼眺望绿水青山,可以陶冶情感,在赏心悦目中派遣闲愁。但作者为了学画,既放弃登阁望山,与大自然晤对的乐趣,又谢绝了人事往来。诗人有意杜绝纷扰,创造可以高度专注某件事的客观环境。在反复研磨自然已有得于心的前提下,以心为师,内营丘壑,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愧”是一个谦词,指自己闭关研磨,勤奋学习,侥幸有所成。三、四句即承此具体写自己的画境已如何日臻神妙,从画的形式看是淡色着墨,让“物”和鉴赏者保持一个最佳的、若有若无的艺术距离,使山色虚无缥缈,以取得更好的审美效果。而“孤峰”的有无却可使人想见在雾漫云遮中,时有峻峭的山峰隐现。把静景描绘成动景。把画写活了,可谓“诗中有画”。读完整首诗才知道:前面“懒望”青山,并非作者不爱青山,而是为了绘出自己心里的青山。而心里的青山是一座带有神秘色彩的“孤峰”。她勾勒得那样神奇美妙,真可谓“江山入画图”10了。
3.对大自然的关照
黄媛介生长在江南灵秀之地,水乡的氤氲之气滋养了她那颗清明温婉的心。她爱这片清山秀水,她画它们,也将它们写入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并于其中寄托自己的悠然情思。皆令之诗除了借景写自己作画的感受外,还有一部分是以景写自己淡然的心境。其中的代表作是《野夕远见》。诗曰:
秋草满池塘,高云合晚凉;水光分远棹,人语近斜阳。
风入单衣冷,花含渚稻香。独当良夜望,星月静繁霜。
此诗写黄昏远眺郊野所见。前四句写已是秋时,池塘的水面长满了枯黄的水草,高远的天空里的云多已经集结在了一起。远眺河面上有一处隐约的帆影,夕阳已经西下,偶有人声传来。接下来由实而虚,从视听之感而及触觉、嗅觉。“风入”承“晚凉”还表示了时间的推移。李白《闺怨》:“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暗示抒情主人公久立的过程。这里同样的暗示了作者的久立晚眺,因为立之久,晚凉渐入,故觉冷;立之久,心渐静,故而嗅觉也分外敏锐,能从花香中品味出稻子的清香来。尾联点出以上都是作者黄昏对独立秋郊的所见、所闻、所感。而俯仰良夜,星月当空,繁霜遍地,最后一个“静”字总揽全诗。我国古代文论认为“虚静”既是鉴赏,也是创作必备的心理状态。“水渟以鉴,火则朗” 11,只有摒除一切功利主义,以澄明的胸怀去观照大自然,才能真正领略大自然的秒趣。作者于是心灵受到抚慰,进入了了“夜阑风静,縠纹平” 12的境地。
4.难免闺怨之作
最后,我们也不得不看到,作为女人,黄媛介亦难免闺怨之作。与一般闺秀不同的是,黄媛介采取了一种很为人非议的生活方式。她先是因夫家贫困而不得被娶,期间有富家爱赏其文才,欲行聘娶,而皆令终于在历尽坎坷后归与杨门。但因生计不保,她不得不以卖画卖文自给,在街头设摊或出入高门,这被时人讥为妇道失守,过于风流。媛介虽生性豁达潇洒但也不免心中寒苦。因为作为那个时代的女子,面对生事不治的丈夫,她失去了一般女子所期望的生活安全感,而直接面对生计的压力,这使缺乏社会角色的皆令心态不免紧张,爱在这样的心田中,显然缺乏生存的土壤,另外,作为一个不得已采取了不同生活方式的早行者,她尴尬而孤独。这种感觉弥漫了她的那首《临江仙·秋日》:
庭竹萧萧常对影,卷帘幽草初分。罗衣香褪懒重熏。有愁憎语燕,无事数归云。
秋雨欲来风未起,芭蕉深掩重门。海棠无语伴消魂。碧山生远梦,新水涨平村。
在此词中,她传写自己孤独、郁闷、倦怠的情绪,她有许多无处放置的幽怨。她独对竹影海棠,懒熏衣香自整,她寂寞而无告的心里充满了否定情绪,她憎厌燕子的呢喃和美,她掩门把自己关在为幽草所包围的空间里,可是又忍不住眺望远处的碧山流云,她在梦想中寄托自己的情怀。她对远景和近景的态度,透露出她对于失意生活和藐远幻想的不同感受。
因为这样的缘故,她很少在作品里传写自己的爱情伤怨,因为她的伤怨内容与一般的女子的有所不同。她们可以名正言顺地抒写自己被冷落的忧愁,而她在生活里的不遇之悲是不能被“合法”传写的,这使她的词境带有一种暗蓄的悲凉,如其《菩萨蛮·秋思》写道:
芙蓉花发藏香露,白云惨淡关山路。愁思惹秋衣,满庭黄叶飞。
绣帘窗乍卷,梦与离人远。秋雨又如咽,魂销似去年。
词写一位“绣窗”中的女子对世界的眺望和对于“离人”的幽梦。这“离人”应该是她那远行求生的丈夫。她没有写自己的缠绵之爱,她感觉到的是这样无奈睽离的“惨淡”“魂销”,即她被抛在可悲生活,无奈婚姻之中的感受。这使她的词境带有一种淡白的烟气,那是萧条之气的流动,是对无奈者那种四顾失落的幽怨之情的溶溢。
四
历代以来,女子多囿于庭院之内,故其作文大都不出与闺闱之事,艺术风格也相对比较单一。皆令由于其特殊的人生经历,使她的文学作品在题材上有所突破,这在第三部分当中已经有分析了。同样,特殊的个性气质也使她的诗文表现出独特的艺术特色。
第一,媛介的作品从总体上来看,呈现出一种“怨而不怒”的风格。其诗风充分体现了“温柔敦厚”的诗教宗旨。其词风则介于豪放和婉约之间,体现出清虚骚雅、清峭苍然的感觉。除诗词外皆令亦擅赋,王士祯称其“作小赋有魏晋风致”13。同样,,她的赋也体现了“怨而不怒”的风气,清人王士禄的《然脂集》,收其赋六篇,皆至为珍品,其中最为时人称道的是《闲思赋》。截其中一段而视曰:
惟古人之不作兮,咏遗篇之渺茫;意欲欻举而无舍兮,心远降而自伤。何伊人之不多怀兮,托幽会于灵神;故素所悦爱兮,冀一见而相亲。致微辞而献诚兮,竟不接而弃我;眷彼美而长怀兮,竭平生而增慕。既不察余之衷情兮,何踌躇而不去?诵诗书以自陈兮,使君王之道光。接一语以迥隔兮,怅永昧于椒房;身欲去而顾留兮,羡浮云之飞扬。曾不得而相抗兮,渺一世而沈藏。何慷慨之不绝兮,人各具此深情。不延赏于君德兮,机关内伤怀于友生。固陈迹之可哀兮,当新怨之未平。怪清风之夜吹兮,音声凄而不绝;情惨怛而易增兮,心惆怅而焉歇?保高人之胸襟兮,虑已开而更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