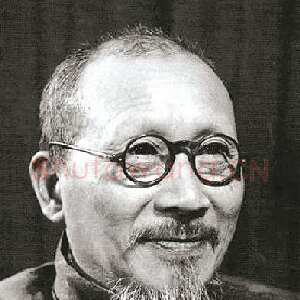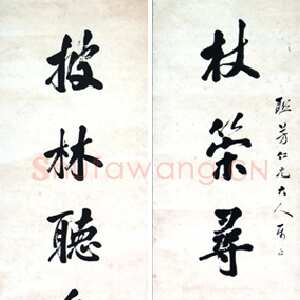名称:最善本淳化阁帖
分类:书法文摘
备注说明:书法百科知识
二○○三年,上海博物馆斥巨资四百五十万美金,从美国购回中国最早书帖集成《淳化阁帖》宋代原版。过了一段时间,又把这套“祖帖”《淳化阁帖》起名叫“最善本”。既是“祖帖”,则绝对是最善本,何必又专门起名为“最善本”呢?汪庆正馆长出面说明,虽然四、七、八三本是“祖帖”,但第六本可能是“泉州本”,不是“祖帖”,虽然如此,四本摆在一起,仍然是留在世界上最好的本子,没有比它再好的了,所以叫“最善本”。
那么,这一套《淳化阁帖》的残卷是否是所谓的“祖帖”或者“最善本”呢?笔者研究的结论是,这四本《淳化阁帖》,完全是几种不同的版本拼凑而成,没有一册是所谓的“祖帖”。
综合启功先生和上海博物馆专家的意见,说这四本是“祖帖”的理由主要是以下三条:一、有银锭纹或横裂纹;二、流传有绪,先后经宋贾似道、元赵孟頫收藏,而且是明末清初收藏家孙承泽的藏品,并有两件宋人的题跋;三、“字极丰穰,有神采”,这是孙承泽等人说的“祖帖”的特点,现这四本符合这一特点。
下面分别予以讨论:
一、所谓这几本帖有前人说的“银锭纹”,因此是原版。实际上,所谓的“银锭纹”,无非是传说而已,并无确据。应该说,《淳化阁帖》的刻板到底是木板还是石板到现在也并无权威的结论。
如果是石刻,则任何带什么“银锭纹”的可以肯定是翻刻。因为石刻是不可能有什么“银锭纹”的。
查“银锭纹”之说最早见于南宋汪逵及南宋赵希鹄所言。南宋曹士冕《谱系杂说》亦云:“绍兴中,以御府所藏淳化旧帖刻板置之国子监,其首尾与淳化阁本略无少异。当时御府拓者,多用匮纸,盖打金银箔者也,字画精神极有可观。今都下亦时有旧拓者。原版尚在,迩来碑工往往做蝉翼本,且以厚纸覆板上,隐然为银锭痕,以惑人,第损剥,非复旧拓本之遒劲矣。”
《淳化阁帖》系北宋淳化三年(九九二)所制。汪逵是南宋孝宗(一一六三—一一七四)时人,赵希鹄是南宋理宗(一二二五—一二六四)时人,曹士冕也系理宗时人。他们写书的时候,离《淳化阁帖》已经有近二百年了,所以,其记载应多是道听途说,可信度不高。而离《淳化阁帖》最近的欧阳修(一○○七—一○七二)和黄庭坚(一○四五—一一○五)从没有说过什么“银锭纹”之类的话,黄庭坚也只是说了一句“有多木横裂纹”。而黄讲上述话时,版如果未如一般人所说的被焚,距淳化也已有近百年之久,故有“横裂纹”是正常的。如庆历年间即被火焚,离淳化只有五十年,更谈不上有什么银锭纹!直至摹刻《大观帖》,北宋灭亡,《淳化阁帖》版彻底消失,从没有什么人有“银锭纹”之说。从情理上分析,可能是南宋时汪逵们看到了黄庭坚的这番话,于是就想到了木裂肯定要用东西连起来,南宋时瓷器比较发达,瓷器坏了就用钉锔起来,而皇家用的钉比较高级,于是就发明了“银锭纹”这个词。从上面引述的曹士冕的《谱系杂说》里面的一段话还可看出,在高宗绍兴年间(一一三一—一一六一)初刻《国子监本淳化阁帖》时尚无甚么“银锭纹”之说,而一百年后的理宗时期就有人用假“银锭纹”来冒充“祖本”了。从此以后,宋元明清,如要翻刻《淳化阁帖》,最简便的,也是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搞什么“银锭纹”或者“横裂纹”以眩人耳目,冒充“祖本”。
总结以上所述,笔者认为,恰恰有“银锭纹”,反而可证明是南宋后的翻刻本!
二、流传有绪。如果该本真的流传有绪,当然也是有力的证明,但仔细分析,似乎能够确信无疑的可信的记载是从清李宗翰(一七六九—一八三一)开始的,以前的记载,似乎都有疑问。
(一)认为经过宋贾似道收藏,根据主要是有贾似道的三种收藏印记。经辨识,其中第六卷末页上的“封”字(或认作“长”字)印肯定是假。因查传世名迹,所有有“封”字的帖,上面的“封”字都是一致的,而且都是与“悦生”瓢印盖在一起的,一般是“悦生”印在上,“封”字印在下;或者,“悦生”印在前,“封”字印在后。唯独此“祖本”上的“封”字笔画长短有异,而且单独使用,显然为假。另外,第四、第七、第八卷的卷末都有“悦生”印,与“封”字脱离而单独盖在卷末使用,也显然令人起疑。
(二)第六卷上有一“大雅”长方印,上博说是赵孟頫的印。经查赵孟頫自书的传世名迹及经其收藏过或鉴定过的其他名迹,发现盖的“大雅”长方印与上述第六卷上的“大雅”印明显不同,第一,上述各帖印的字迹完全一致,与第六卷上印的字迹明显不同;第二,赵孟頫的“大雅”印都是和其“赵”字方印或者“赵氏子昂”等印一起使用的,与第六卷单独使用“大雅”印不同。因此,第六卷上的“大雅”印非常可疑。当然,有人举出传为王安石的《楞严经旨要卷》上盖有与第六卷上一样的“大雅”印,似乎可证明该印不是孤证。但与上述的大量的另一种“大雅”印相比,仍显证据不足。而王安石书卷上有同样的印章,只能说明这两件东西可能都经过了一个人的手。总之,用一方值得怀疑的印章来肯定第六卷经赵氏收藏过,证据显然不足。
(三)上博本第六、第七、第八卷上都有明末清初收藏家“孙承泽印”记,因此认为该三卷为孙承泽所藏。
根据孙氏记载,其所藏的第六卷上既无赵孟頫的“大雅”印记,又无贾似道的“封”字印记。
第六卷中的所谓的“北宋人题跋”,即使是北宋人的真迹,但从文字内容来看,决非指的是此第六卷,因其文字为“余所藏本首幅有横裂纹 —— 第一、第七、第十七皆有横裂纹”。
查现第六卷第一、第七、第十七页皆无横裂纹,怎么可能是指的此第六卷呢?
据孙承泽记载,第六卷上应有“翰林学士院印及绍圣三年冬至前一日装题字”,现在皆无。
因此,孙承泽说有翰林学士院印及绍圣题识现在却无,佚名宋人题识说三页有横裂纹现在也对不上号,没有记载却又多出了贾似道假的“封”字印及赵孟頫假的“大雅”印记,这么多的疑问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这本“最善本”第六本不是孙承泽收藏过的第六本,上面所盖的“孙承泽印”是假的!
根据孙氏记载,第八卷中并无什么南宋宰相王淮的题识,而现在却多出了这么一段题识,另外,从其文字的内容来看,他明明说的是他观看的这一本是“蝉翼本”,而现在的第八本,虽然“石花”略多,但明显仍属浓墨本,与我们平常指为“蝉翼本”的完全是两回事。那么,什么是“蝉翼本”呢?看一看明华夏的《真赏斋法帖》就清楚了。所以,王淮的这件东西,即使是真的,也根本不是现在的第八卷里面原有的题跋,应该是其他卷里面的内容。所以,由于孙承泽在其书中从来没有提过这么重要的王淮题跋的事情,再加上第六卷的论证中已证明了“孙承泽印”是假的,因此这个第八卷也不是孙氏收藏的。
既然第六、第八两卷皆假,则第七卷上的“孙承泽印”记肯定也是假的,而且,从纸色和字迹分析,可轻易地辨识出是两种不同的版本拼接而成。
至于第四卷,由于没有孙氏印鉴,故肯定未经孙承泽收藏。虽有董其昌的一张便条和翁方纲的一段短跋,但评价显然不高,绝无判定是“祖帖”的意思。
第四卷上“贾似道图书子子孙孙永宝之”印,此印在其他传世书画上从未见到过,而且这么长的印文内容似乎只有在明清时才有,所以可信度很低。
至于字体是“丰穰”还是不“丰穰”,是“有神采”还是“无神采”,这是一个见仁见智很难说服人的事情。何况这种说法只是孙承泽等个人的看法,他们往往是自己得到了几本自认为好的版本,然后就依此总结出所谓“祖本”的特点,这种看法是没有可靠的根据的。同样的,说是有“大字的卷数和版数”的就是祖本,也是南宋汪逵的个人看法,他的时代离《淳化阁帖》的初版已经有两百年了,当时已经有几十种阁帖的翻刻本到处传播,什么是“祖本”已经很难辨别清楚。何况,正如伪造“银锭纹”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一样,伪造“大字卷数版数”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这样说来,有无“银锭纹”不能作为证据,“流传有绪”又有可能是伪造的,“是否丰穰”、“大字卷数版数”也是个人的一些并非权威的看法,那么,什么样的版本才是真正的“祖帖”呢?难道这是一个“虚无”的东西吗?
显然,要解决此问题,最可靠的辨别方法,就是以一部“祖帖”为标准,将所要辨别的帖进行仔细的比对,一致的,起码就有可能是“祖帖”,再看其他条件进一步分析。不一致的,就肯定不是“祖帖”,差异越大,说明翻刻的次数就越多,离祖本就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