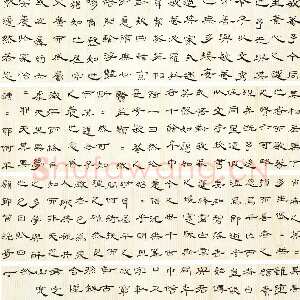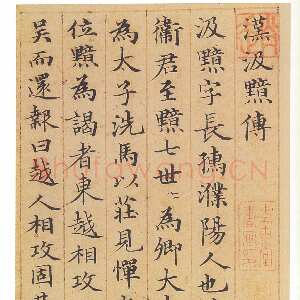名称:从包世臣论其书法批评观
书法家:包世臣
分类:书法文摘
备注说明:书法百科知识
范的,生卒年不详,唐文宗时人。宋赵明诚《金石录》载,唐《阿育王山常住田碑》,开元中齐万融撰,徐峤之书,碑毁,太和中明州刺史于季友作后记,属处士范的重书之。范的为包世臣所推重,在《艺舟双楫·述书下》中评其:“……中更丧乱,传笔法者唯明州布衣范的、洛阳少师两家。范之《阿育王碑》,行间茂密。”后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卑唐第十二》中延续包世臣的说法:“范的《阿育王碑》,亦有南朝茂密之意。”叶昌炽《语石》评其“萧诚以后,学王书者第一。”明驼,骆驼。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十六引《木兰篇》句作:“愿借明驼千里足”,并谓驼卧时,腹不贴地,屈足漏明,则行千里,故称明驼。舒步,徐徐、迟缓之步。轩昂,峻高貌,扬起貌,形容气概不凡。此句意为:范的的书法如骆驼缓步而行,峻高而气概不凡。
玉局如丙吉问牛,能持大体;
此评苏轼,因其曾官提举玉局观复朝奉郎,偶有人以“玉局”称之。丙吉(?—前55),西汉大臣,字少卿,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本为鲁狱吏,累迁廷尉监,治巫蛊之狱,后任大将军霍光长史,建议迎立宣帝,封为博阳侯,任丞相。问牛,典出《汉书》七四《丙吉传》,汉宣帝时,丙吉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问牛行几里,或谓牛喘为细事,吉曰:“……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时气节失,恐有所伤害也。三公典调和阴阳,职当忧,是以问之。”后因用为官关怀民间疾苦的典故。此句意为:苏轼的书法如西汉大臣丙吉问牛,关怀民间疾苦,而得其大体。
包世臣从25岁学习苏轼的《西湖诗帖》开始,此后一直对其推崇备至,吴德旋说:“慎伯论书,于唐人后推东坡、思白二家。其言以为东坡雄逸,思白简淡,非馀子所及。”又云:“自兹以降,宋之东坡、明之香光亦臻妙悟。东坡云:‘我虽不善书,解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香光云:‘画中须直,不得轻易偏软。’探厥词旨,可谓心通八法者矣。”可见他对苏轼、董其昌的崇尚。
端明如子阳据蜀,徒饰銮舆;
此评蔡襄,因其曾官至端明殿学士,人称“端明公”。子阳,即公孙述(?—36),字子阳,东汉扶风茂林人,王莽时为导江卒正。后起兵,据益州(今四川),自立为蜀王,建武元年四月称帝,号成家,建元龙兴。建武十二年为汉军所杀。銮舆,天子之车驾。此句意为:蔡襄的书法如公孙述占据四川,徒饰有豪华的天子车驾。
山谷如梁武写经,心仪利益;
此评黄庭坚。梁武,即梁武帝萧衍(464—549),南兰陵人,长于文学、乐律、书法,信佛教,三次舍身同泰寺,寺院遍境内。经,指佛经。利益,佛教用语,犹言功德,指有益于他人的事。《法华文句记》:“功德利益,一而无异,若分别者,自益名功德,益他名利益。”此句意为:黄庭坚的书法如梁武帝抄写佛经,内心向往有益于他人的事。
海岳如张汤执法,比用重轻;
此评米芾。张汤(?—前115),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武帝时历任廷尉、御史大夫等职。建议铸造白金及五铢钱,并支持盐铁官营政策,制订“告缗令”(对田宅、货物、车船、畜产等征税的法令),以打击富商大贾。主办许多重大审判案件,用法严峻,曾和赵禹共同编订律令,撰有《越宫律》27篇。此句意为:米芾的书法如张汤执法审案,用法严峻,而轻重适宜。
包世臣对米芾书法的“跳荡之习”是轻视的,这在他的言论中时有涉及,他说:“襄阳侧媚跳荡,专以救应藏身,志在束结,而时时有收拾不及处,正是力弱胆怯,何能大字如小字乎!”包世臣又有:“米海岳《九歌》、赵松雪《黄庭内景经》,皆能不失六朝人遗法,但其他书不能称是,遂为识者所轻。”
子昂如挟瑟燕姬,矜宠善狎;
此评赵孟頫。瑟,古代一种弦乐器,形似古琴。燕姬,燕地的美女。唐李白《李太白诗》七《豳歌行·上新平长史兄粲》:“赵女长歌入彩云,燕姬醉舞娇红烛。”矜宠,自恃有宠而骄。《新五代史·安重诲传》:“虽其尽忠劳心,时有补益,而恃功矜宠,威福自出”。狎,有亲近、轻浮之意。此句意为:赵孟頫的书法如挟着古琴的燕地美女,恃宠而骄。
包世臣对赵孟頫是最为鄙视的,他对赵字给予批评:“若以吴兴平顺之笔而运山阴矫变之势,则不成字矣。”吴熙载问包世臣“匀净无过吴兴,上下直如贯珠而势不相承,左右齐如飞雁而意不相顾。何耶?”包世臣回答说:“吴兴书笔专用平顺,一点一画、一字一行,排次顶接而成。古帖字体大小颇有相径庭者,如老翁携幼孙行,长短参差,而情意真挚,痛痒相关。吴兴书则如市人入隘巷,鱼贯徐行,而争先竞后之色人人见面,安能使上下左右空白有字哉!其所以盛行数百年者,徒以便经生胥史故耳。然竟不能废者,以其笔虽平顺,而来去出入处皆有曲折停蓄。其后学吴兴者,虽极似而曲折停蓄不存,惟求匀净,是以一时虽为经生胥史所宗尚,不旋踵而烟销火灭也。”
伯几如负暄野者,嘈杂不辞;
此评鲜于枢。负暄,曝背取暖。嘈杂,吵闹声。此句意为:鲜于枢的书法如光着脊背晒太阳的山村野夫,吵闹声不断。
京兆如戎人砑布,不知麻性;
此评祝允明。砑布,用石头在布上碾磨使密实发亮。麻,指大麻。旧属谷类植物,今属桑科,皮韧,沤之可织布,雄麻质佳,雌麻粗硬不洁白,用于丧服。此句意为:祝允明的书法如士兵碾磨布匹,不知道麻的特性。
宗伯如龙女参禅,欲证男果。
此评董其昌。龙女,神话中龙王的女儿。佛经中有龙女成佛的故事,《法华经》言娑竭罗龙王之女,八岁领悟佛法,现成佛之相。《法华经》又云:“龙女欲成佛,必将女转男身是也。”可见其修持和证果。
吴德旋说:“慎伯论书,于唐人后推东坡、思白二家。其言以为东坡雄逸,思白简淡,非馀子所及。”可见他对董其昌的欣赏。包世臣认为:“华亭为近世书宗,……华亭受箓季海,参证于北海、襄阳,晚皈平原,而亲近柳杨两少师,故其书能于姿致中出古淡,为书家中朴学。”同时又认为:“然能朴而不能茂,以中岁深襄阳跳荡之习,故行笔不免空怯,去笔时形偏竭也。”他对董其昌中年以后学米芾表示出不满。他还认为:“坡老、思翁,有意复古,而苏苦出入无操纵,董苦布置不变化”,对董提出“布置不变化”的看法。
二、从二十家品评看包世臣书法批评观 包世臣这种以形象比喻的叙述语言和批评方式,在书论中出现较早的见于梁代袁昂的《古今书评》,如“索靖书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梁鹄书如太祖忘寝,观之丧目”等等。此后梁武帝萧衍的《古今书人优劣评》、唐代孙过庭的《书谱》、窦臮的《述书赋》、张怀瓘的书论、宋代米芾的书论中多有出现,对于处于清代复古潮流中的包世臣来说,运用了袁昂《古今述评》的方式对二十家的书法进行品评是顺理成章的,后来康有为又从直接模拟包世臣的这种叙述方式,见于《碑评》。
首先,包世臣对唐代书家及其书法表示出由衷地赞叹:“永兴如白鹤翔云,人仰丹顶;河南如孔雀皈佛,花散金屏;王知敬如振鹭,集而有容;柳诚悬如关雎,挚而有别;薛少保如雏鹄具千里之志;锺绍京如新莺矜百啭之声;率更如虎饿而愈健;北海如熊肥而更捷;平原如耕牛,稳实而利民用;会稽如战马,雄肆而解人意。”这说明了唐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从他的言论中,我们得知他喜欢唐碑,是因为他认为初唐书法保持了“中实”之法,加上唐碑能壮帖之势而宽帖之气。最重要的是他认为:“大凡六朝相传笔法,起处无尖锋,亦无驻痕,收处无缺锋,亦无挫锋,此所谓不失篆分遗意者。虞、欧、徐、陆、李、颜、柳、范、杨,字势百变,而此法不改。宋贤唯东坡实具神解;中岳一出,别启旁门;吴兴继起,古道遂湮。”“篆分遗意”成为他书法审美的最为重要的标准,也成为他书法批评的重要标准。
其次,他对宋人的态度则是有褒有贬:“玉局如丙吉问牛,能持大体;端明如子阳据蜀,徒饰銮舆;山谷如梁武写经,心仪利益;海岳如张汤执法,比用重轻。”他认为宋以后古法不传,故对宋以后书家大加贬低。当然,这其中对他所景仰的苏轼是例外的,他认为宋以后“篆分遗意”流失,唯苏轼“实具神解”,而米芾一出“别启旁门”,赵孟頫继起,“古道遂湮”。这是他推崇苏轼和反对其他宋人的理由。
再次,对元、明书家则以贬为主:“子昂如挟瑟燕姬,矜宠善狎;伯几如负暄野者,嘈杂不辞;京兆如戎人砑布,不知麻性;宗伯如龙女参禅,欲证男果。”对于赵孟頫的书法,包世臣持激烈的反对态度,这当与时风的崇董、崇赵有一定关联,他是对康乾时期的董赵书风的一种反叛。当然,这主要与他的书法审美观有很大关系,除了他认为赵孟頫篆分遗意的失去之外,还认为用笔平顺、结字匀净,没有能领会王羲之的矫变之势。对于鲜于枢、祝允明更是大为贬低,认为毫无可取之处。这是对“自唐迄明,书有门户者廿人”的品评,对于其他书家,从包世臣的态度而言,更是不值一提。
实际上,宋代《淳化阁帖》出现以后,宋、元、明书家多有取法,于是帖学大兴,这是书法史的一段史实,而阮元认为《淳化阁帖》“展转钩摹,不足据矣”,从《阁帖》失真说明帖派师法对象不可靠,又认为“所称锺王者,其伪爽然可见”从王字应有隶意为推翻王羲之寻找借口,最重要的是他认为“《阁帖》盛行,北派愈微矣”可见否定《淳化阁帖》最终是为了推出北碑。包世臣虽没有直接否定《淳化阁帖》,但他认为“欲见古人面目,断不可舍断碑而求汇帖”,与阮元观点一致,再认为:“余远追微旨,结体则据枣木本《阁帖》,用笔则依《秘阁黄庭》、《文房画赞》,而参以刘宋《爨龙颜》、北魏《张猛龙》两碑,以不失作草如作真之意”他欲以北碑来改造王羲之帖,其指归实际上有相同之处,所以,包世臣对宋以后书家的否定也就顺理成章了,这和他的推崇北碑的思想就是完全一致的了。
从上述评论来看,包世臣的批评观已经很清楚,他所肯定的是唐人(包括唐以前),对宋(除了苏轼)、元、明书家给予了普遍的否定,这是基于篆分遗意的审美标准,也是他推崇北碑立场的反映,这样,他的批评观就是站在碑学立场来作评判的,本文认为这不是一个历史的态度,他是戴着有色眼镜来作批评的,这种批评容易造成不能历史地、客观地看待问题,也就会作出不准确的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