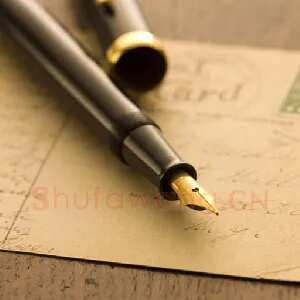名称:钢笔行草书和毛笔行草书创作之比较
书法家:朱以撒
分类:硬笔文摘
年代:当代
出处:中国钢笔书法艺术
备注说明:硬笔书法文献
新时期以来的钢笔书坛和毛笔书坛在创作上有着一个很相近的特点,那就是行草书创作的勃兴和繁荣,十年来创作作品之多,远远胜过了其它书体。就书法家队伍来说,不少毛笔书法家也时有突入钢笔书坛的情形,有的甚至参与了其中的竞赛、展览以至书写字帖,成为其中的热心者,而钢笔书法家也有感到创作的进展需要毛笔书法辅助而兼涉毛笔书法创作的,这相互交叉的“两栖书家”是越来越多了起来。我们对钢笔行草书和毛笔行草书在创作中的比较,不在于要比较二者的尊卑高下,而意在比较中找出它们的不同之处,使这种比较成为向前发展的一种参考。
首先是二者的取法有较大的不同。毛笔行草书有着深厚的取法源,并且可以分为雄伟和优美两大流派,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优美者可以从王羲之始一脉流贯、南朝书风、智永、唐李世民、褚遂良、虞世南、陆柬之、孙过庭、李邕,五代杨凝式,宋李建中、蔡襄,元赵孟頫,明文征明、王宠、沈度、沈粲、唐寅、董其昌、黄道周,清王文治及大量“阁体”,以及现代沈尹默、潘伯鹰、白蕉诸家;而雄健者又可以从王献之而至盛唐颜真卿、张旭、怀素及稍后的柳公权,宋之苏轼、米芾、黄庭坚,元之鲜于枢、杨维帧、释溥光,明之祝允明、徐渭、邢侗、米万钟、张瑞图、王铎,清之傅山、赵之谦、康有为以及现代的于右任、沙孟海诸家。取法源的博大深邃,自然就形成了风格繁衍的多样多种,它们之间又经书法家的交叉融合,以至于风格类型的无穷。当代书坛上有书风不断转向的势态,书坛人士并为此感到忧虑,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则可以说明毛笔体法可以取法者甚多,任何转向都可以有足够的法帖为人效仿,因此尚北魏碑板也罢、盛写经小楷也罢,兴行草小品也罢,都有十分优秀的法帖使学习者得以效法。钢笔书法的取法则不同,行草书的学习主要来自于对今人中的优秀行草进行学习,即学习钢笔行草字帖。有许多字帖本身的风格我们很难找出古人的影子,也就是说这些作者本身也没有学习过古代书法范本,他们的成功靠得是自身琢磨、持之以恒的练习而达到的,但是他们的成功并没有与古人沟通。
书法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技能,从小就进行着书写,不知不觉中,他们之中的一些有心人,聪慧者也是能够悟出一点用笔、结体的道理的。熟能生巧,天长日久也就能够逐步达到理想的境界了。这里很有一点“无师自通”的味道,尤其是新时期以前钢笔书法水波不兴,谁的笔迹优秀便可以为师,取法方便,尽是身边师友,这种取法乎近的因素特别明显,也是毋庸讳言的。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许多钢笔书法作者都有一个明显的标志,那就是喜欢将自己的作品挂在某一位古代书法家风格的羽翼上,而实际上,我们从这些钢笔书法作品中又全然看不出有什么特色。由于古代行草书作品相当丰富,行草无所不在,因此附翼于这些书法家,似乎就提高了自身的格调了。我们看到的自称学二王、苏、米的作者甚多,从作品来看,仍然是学习当代优秀钢笔书法家的作品的。许多作者感到,钢笔行草书取法源较小,就当代钢笔行草书较突出者并逐渐建立领袖地位的,不过数人。他们长期地从事钢笔行草书法的创作与研究工作,并且以自己的突出成就影响着当代钢笔书坛的众多学习者。值得提出的是,他们的年纪都较轻,钢笔书坛的行草好手很少是象毛笔书坛的耆宿那样的白发苍苍,他们的年青,使他们较少顾虑而一直呼啸着向前。由于有这么一批优秀的钢笔行草书家,学习者更多地从他们的作品人手,由于同处在一个时代,同时接受某一种文化思潮的影响,上手较快,没有几年时间,就出现了一批相近于任平、王正良、骆恒光一类书风的作品。如果在众多的行草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出,风格是不够多样的,即使是出版的许多行草字帖,也都大同小异,这就给人一种“屋下架屋,愈见其小”的感觉,使钢笔行草书作品在数量众多的情况下,精品却甚为有限。
有一部分作者从师法今人钢笔行草书的狭窄处境中脱身出来,试图进入广阔的效法毛笔行草书的领域,这一尝试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这种考虑和行动是基于几个方面的,一方面是舍弃当代钢笔行草书的效仿而转向古代行草书,这时的规格就远胜一筹了,甚至学成之后可以超越当今的钢笔行草书家,宁可为古人奴也不为今人所囿。另一方面是从事毛笔行草书字帖的效法,可以近古人而远今人,毕竟古代书法作品是一个浩瀚的大海,而在具体的效法中,使自己的钢笔行草书具有毛笔书法风韵,不是为人所孜孜以求的么?还有一方面是力求钢笔行草书的毛笔化,尽心尽意地追求毛笔书法的全部特点,并以逼真为成功标准。这些效法的思索,不能说没有意义,但又不会是完美的,甚至缺陷也很多。毛笔书法是一脉相承的,不仅工具相袭,范本也是脉络清楚,分支明了,而钢笔书法与之相比不仅有着工具的迥异,还有线条表达方式的差异。一些对毛笔书法毫无认识的作者却没有去思索这其中的不同,而是以为随取古人行草一家便可以临写无碍,这种想当然的取法自然使许多作者的工作徒费年月,甚至不如他们取法当代钢笔行草书的效果。但是有一种现象却很令人振奋,一些长年从事毛笔书法创作的书法家,他们并没有认真地临写过什么钢笔书法字帖,只是很自然地将毛笔行草书的运笔、结体、章法等特点转移过来,很自然地,他们的行草书也成了上乘之作。有一种说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即毛笔行草书创作优秀者,驾驭钢笔行草书易如反掌,而钢笔行草书能够创作自如者,却可能在毛笔行草书创作上无所适从。尽管创作者不一定都要成为二柄书家,也不一定以毛笔行草书来统辖钢笔行草书,但是,如果要以古人行草为范,也就需要有相应的实践经验,这种经验不能是照搬,而是一种融化、转移,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渗入。许多书法家的行草书与他们的钢笔行草怕是极为相近的,不仅是形态,而且是神态。而纯粹为实用于钢笔书法而临写的,往往就别扭、生硬感,尤其在转折之处,这种缺陷就更明显了。
笔者曾经论述过钢笔书法不是要与毛笔书法较其高下,这是因为各自有不同的发展方向,钢笔书法不必非如毛笔书法不可。现在钢笔书法作者都有一种感觉,以为作品中有毛笔书法韵味为佳为上。这种韵味从何去认识,又从何去把握呢?这只能是比较长久的研习、体验、揣摩、感受才可能得到。这种渗透是隐形的,如果没有深入进去,慢慢地浸润,无论如何也无从谈到毛笔韵味。韵味的融入和技巧的把握是不一样的。一位作者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把握住古代某一家行草书之字形、取势,这是可以凭借归类、分析、总结来达到的,许多取法毛笔行草书的作者,在他们的钢笔之下出现的线条不乏潇洒、放纵、秀逸、委婉,但要认为有毛笔书法韵味则是一种奢求,这是说毛笔书法韵味不是效法古人法帖便可得之,而是说它的渗入是需要有一个比较长久的过程。这是一种影响。也应该在学习的后期才能出现。在众多的古代行草作品面前,钢笔书法作者会感到有一种非效法不可的压力。这种压力除了来自于向更高一层次攀登的愿望之外,也不乏有正统、非正统之间的心理。因此钢笔书法作者又喜欢常常引用甲骨文为最早硬笔书之例,这种心理,又无不为钢笔书法在人的观念中的地位息息相关。
当然,如果从事毛笔书法创作的好手也能兼顾钢笔书法,那么其间的差异心理就会减少许多,但在壁垒分明的毛笔书法和钢笔书法领域中,钢笔行草书的作者仍然需要从钢笔书法的特性出发,取法毛笔书法字帖并不是主要的,一位毫无毛笔书法功底的作者要以钢笔摹写毛笔书法字帖,其困难也是可想而知的,这也并非有向毛笔法帖效法的愿望便可得之、便可解决的。重要的还在于把握线条,提练线条上面。钢笔书法毛笔韵味是第二义的,能够达到的也只是对于书法有较深感觉的作者。钢笔行草书的便捷、灵动性相当高,它的线条属性应该是钢笔的,在热衷于取法毛笔书法字帖的背后,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作者的心理,有时候会觉出这其中缺乏一种高层次的理解,创作主体受到了来自于并未成熟的、带有较强的实用功利性的侵袭和干扰,取法古人法帖是做为一种标志而存在的,这种取法未经过细致的梳理,随着也带来了焦躁不安的情绪,反而无益于效法的按部就班,从这一点来说,取法当代钢笔书法的最佳范本,应该是最切实可行的。

在钢笔书法与毛笔书法的表现形式上,二者也有着比较大的差别。毛笔行草书有一个由大到小的创作形式改变过程。前几年的毛笔行草书创作,由于受到北方书坛的影响,行草风格偏于粗犷、豪迈,以气势为重而不太注重细节,同时以幅式的巨大烘衬了这种风格的特征,使它们在一个展室里尤其显得注目的王者气概,而后,这种粗犷豪放的形式由于细节的处理欠细致,同时也因气势对欣赏者感官的刺激过于粗糙、强烈,行草书书法家又转向于小品行草的创作,精心地刻划每一根线条,使一笔一划的表达尽量完整、细腻。这样,行草小品又以小巧玲珑、清新细微的面目出现了。在纸质上,毛笔行草由多以白色宣纸创作转向了仿古宣、洒金笺,这些色宣古色古香的气氛,使作品弥漫着一种古老苍茫的情致。同时在创作的趣味上也由庄重往恢谐、随意方向发展,越加显出轻松和愉悦的闲适特点。钢笔行草书法的形式变化不象毛笔行草书那么明显,而且.也是不同步的。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钢笔行草书有越写越长,篇幅越来越大的趋向,有的作者甚至以数张纸相接来进行长篇创作,而字径也有不少受到取法毛笔行草的影响,意欲以其大来张目,他们大都离开了钢笔,而自制竹笔、木笔等笔径粗大的工具。但是这些作品的效果反而不如集中于一张十六开纸面上的来得优越。钢笔书法为天然的小品,雄壮豪放也只是相对而言的,书写的篇幅拉长,往往暴露了作者许多弊病,也分散了作者的精力,无法展示出其中最精粹的部分,它的拉长,并没有在精神上给欣赏者以更多的信息量,而只是刺激欣赏者的感官而已,尤其是有些作者以粗大的竹笔创作出的大字,意欲等同于毛笔行草书的字径,这是认识上的一个很大偏颇,认为感染力取决于大字。与之相反的是钢笔书法中的微型小品也出现了,这种作法很明显地受到了毛笔行草小品的影响,这也是一种不与钢笔书法特点联系的一种做法。
在一幅作品里字数寥寥,又由于字径小而感到单薄,即使再精彩也有寥落之感,精雕细刻般的微书,给欣赏者一种工艺品的感受,欣赏也有着一定的难度。钢笔行草书的篇幅究竟以何为适宜呢?自然不能有个硬性的规定,但也并不是因此任何幅式都合适。钢笔行草作品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它都是小品式的,即便形成了小品系列,也难以形成一种黄钟大吕式的轰响,人为地揠苗助长以求恢宏是不可能的。同样,缩小字径或以少字数出现,也不适宜于钢笔线条,一方面是行草书中灵秀飞动的线条会由于字径缩小表现得不那么淋漓尽致和清晰无误:另一方面,少字数行草又通常求外张而显得笔力难济(这自然也与纸质、笔性有关)。那些控制在十六开纸面,以二、三百字作为一个创作单位,每一个字一厘米见方,这样的创作也是非常符合欣赏者长期形成的欣赏习惯的。钢笔行草书的表现幅式应有所节制,要克服那种大而无当、小而微弱的缺陷。毛笔行草书由于墨趣的关系,可以表现为极大的幅式,也可以表现为小品,这是诸体中抑扬伸缩最灵活的部分,也是钢笔书法不可也不必思齐的,否则,会使这种行为本身染上了一种矫饰、牵强的色彩。钢笔行草书法无论篇幅是大是小,都没有“墨分五色”那样的墨趣效果(当然也有些作者试图用宣纸来表现,但依笔者来看,却是末技之一种),但却可以运用钢笔硬的特性创造出不同痕迹的行草书。一般地说来,人们更注重于钢笔笔尖的处理,使之出现粗细差距较大的线条,却忽视创作中用纸衬托的这一层关系。实际上,一些钢笔行草书家已经在他们的笔迹中表现出来了。有的笔迹极细,有的笔道又极粗,除了与按笔的轻重有关外,余下的就是纸张下面的铺垫了,这方面还是秘而不宣。
一张稿纸,没有晕散墨水的性能,如果放置于硬物之上(如玻璃板、桌面),那么书写出来的线条是比较细硬尖锐的,透过一层薄薄的纸,实际上是笔和硬物的直接对垒,字迹缺乏厚重感,流露着尖刻和硬挺。如果在纸上垫上二、三层纸,效果就有了改观,以至于人们通常在一本稿纸上创作,一俟创作完毕才揭下,虽然已成为习惯,却很有一定道理。由于有了一定厚度的铺垫,钢笔就不再是与硬物对垒了,而是与软物(如纸垫)接触。这时,只要细致观察,便可以感觉到创作时的手感弹性增强了,钢笔的提、按也有较大的伸、缩度。加上纸质也有光洁硬滑和粗糙柔腻之别,因此又可以在这种衬垫的纸质上划分出许许多多的层次。一些行草书笔迹的区别,如果说一位书法家的技巧是比较固定的,但是在不同的铺垫之下,却可以出现许多微妙不同的效果。因此,当钢笔书法作者面对毛笔行草书家多方面地选择用笔,多层次用笔眼热之时,有时的效频是没有考虑钢笔行草书的特性而进行的,这就引起了创作的非正常效仿。例如近年来出现的美工笔,实际上就是为追求毛笔行草书法线条的粗细悬殊而设置的,这固然很有刺激性,即使是不习书法者,也可以笔尖翻动写出时粗时细的作品。笔尖的改革,对于表现各种不同形态的线条是有利的,可是,如果注意一下运用这类钢笔书写的线条,相当一部分行草线条是扁平、单薄、粗糙的,如果把用笔的重点不放在研究、感觉线条之上,反寄希望于某一种新工具将减轻或取消这种研究的辛劳,这就妨碍了钢笔书法的发展了。我们看到一些钢笔行草书达到很高层次的书法家。并不使用这样的工具,却极其注意训练线条的把握、提炼,其作品粲然可观,很有神采。这是因为,作为书法家的精神物化形式—线条,除了要有书法所需要的法则之外,更要有神气、韵致、灵性,这就需要行草书家不仅要有写楷书的那种规矩,还要有发挥,有更多的情绪寄托。而线条要能做到寄托情绪,书法家就必须在线条上下工夫。这就如同毛笔书法材料的改造一样,尽管各种毛笔相继出现,尽管各类宣纸多有不同,对书法家的影响是轻微的,书法家们绝不会有很大兴趣来尝试这些新制,因为这种尝试往往干扰了正常书势、手势。钢笔书法行草书创作也如此,过多地在材料上、形式上的翻新,反而是对创作的反动。
其三,关于情感在行草书创作中的运用、抒发以及调控。就毛笔行草书创作来说,人们是一致地认为它无疑是充沛情感最好的寄托形式,只要人们要运用书法创作这一形式来表情达意,那么他就一定非选择行草书不可,这样,行草书就与创作者的情绪最为紧密地连为一体了。在古代论书诗中,许多篇章都借行草论述了这一点,如“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有时兴酣发神机,抽毫点墨纵横挥。风声吼烈随手起,龙蛇进落空壁飞。连拂数行势不绝,藤悬查蹙生奇节。划然放纵惊云涛,或时顿挫毫发,自言转腕无所拘,大笑羲之用《阵图》”。这种创作可谓心手两畅,欣赏者也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在前几年的对钢笔书法是否可划入“书法”这一范畴的讨论中,提出异议者就以钢笔书法不能承受或充分表达情感而立论。情感在钢笔书法与毛笔书法之间,自然是毛笔书法的表达充分得多。创作毛笔行草,字径大,吞吐量大,纵横捭阖不胜淋漓痛快之感,这种情绪传递给欣赏者也是强烈无比的。当年李白看了怀素的狂草创作后就写下了奇丽的诗篇:“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如楚汉相攻战”,当代书法家费新我也谈到他一次看到明代王铎的草书,那种璎络连接、势如破竹的线条使他心潮振荡。钢笔行草书还不能有这样的效果,人们欣赏时赞叹、称绝,在心灵上也只是泛起淡淡的涟漪,不可能有风暴一般的震撼,因此我们看到对钢笔行草书欣赏、评介,也很少用大气磅礴、力能扛鼎这样的字眼。
但是,在我们讨论情绪在行草创作中的作用时,却不能忘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即情绪的表达不一定都是火山爆发一般的猛烈和冲动的,它有时候是以一种潜流出现的,轻缓地、细微地释放,作者在创作中有激情,但并不外张,这种激情的涓涓细流就能够使创作的时间得以延续。由于我们长期眼膺于张旭、怀素这一类书法家那种外张情绪创作,使情绪的另一种委婉的表达方式忽略了。钢笔行草书的情绪表达固然比不上毛笔行草书那么淋漓尽致、倜傥痛快,但却可以用另一种表达方式来进行。情绪的表达有时也需要抑制,人们往往崇仰那种放浪形骸忘乎所以的创作,殊不知没有抑制的情绪,有时如脱僵的野马难以捉控,只凭情绪的驱使而忽略了应有的笔墨。对情绪的认识,不唯书法,在其它艺术门类也有不同的意见,如诗歌创作,有的诗人认为激情创作为佳,“愤怒出诗人,”而有的诗人则认为情绪会杀掉诗的美感,诗人应以情绪平静时创作为优;而表演艺术亦如此,有的演员全身心投入,剧中人物便是演员,难以区别主客,而另有一类演员却在表演中时刻记住自己与角色的区别,做到清醒的表演。可以说这两种不同的创作观都有其独到处,很难区分出孰优孰劣。情绪的充盈有时导致的效果是满纸云烟或粗糙狂放,尽管作者的情绪得到了释放,得到了满足,但是书法创作中所需要的规则却失去了。这样的创作,在作者冷静下来时,也会发现其中因情绪泛滥而产生的大量弊病。钢笔行草书的创作决不是在情绪高涨之下所能进行的,由于字径偏小,过份冲动则字迹颤抖、歪斜、扭曲。一件钢笔行草作品一般为二、三百字之多,书写起来就需要有一个比较沉稳持久的情绪,使作品的完成首尾相衔、前后一致。钢笔书法家如何看待情绪也是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有一句话说得很通俗也相当在理:“鞋紧不紧只有自己的脚知道”,我们宁愿把钢笔行草书与毛笔行草书相对拉开一个距离来认识,否则,在形式寄予情绪这个问题上,往往纠缠于表现的充分与否而自惭形秽,这实际上是十分有害的。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代书坛对于情绪在创作中的作用认识还是很不完整的,又总是以激情来认识创作。钢笔行草书创作在运用情感方面应该有别于毛笔行草创作,是斯斯文文地,而不是风风火火地;是举止有序地而不是醉来纵笔两三行;是精心运筹而不是边幅不修。钢笔书法家应该具有这样的一种情绪制约力,这样,作品线条的把握将会更稳重更沉着。
行草书创作,作于毛笔书坛和钢笔书坛,都是主流,但是二者之间是有着许多区别的。对于钢笔行草书创作的作者,甚至比创作其它书体更容易去与毛笔行草书联系,甚至与毛笔行草书靠拢、思齐,名曰借鉴,实则是照搬套用。不加分析地运用毛笔行草技法那一套也比较明显。这样,势必使钢笔行草创作增强了它的依赖性。本文意在行草创作的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将其不同之处分解出来,当我们站在一定的距离观察钢笔书法创作时,也许会更清楚地认识它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