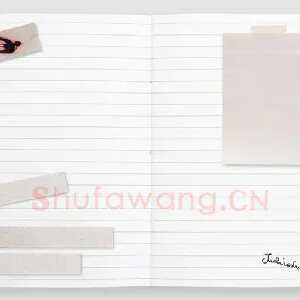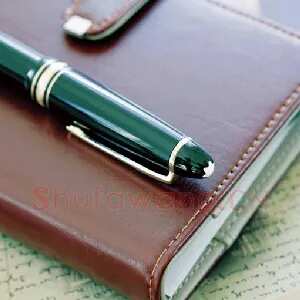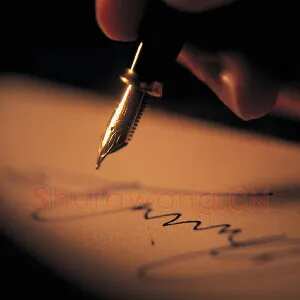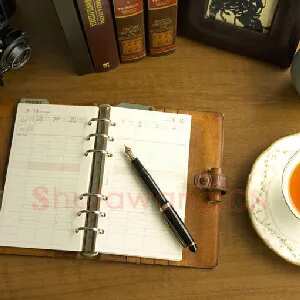名称:发展与环境
书法家:朱以撒
分类:硬笔文摘
年代:当代
出处:中国钢笔书法
备注说明:硬笔书法文献
硬笔书法的发展从形式上来看是很旺盛的。也就是说参与者多、活动频繁,加之参与青年所占比例大,更显示了硬笔书法的活力。我们从一些活动中可以看出,青年作者已经成为硬笔书法群体的主流,这些参与者绝大多数是为了滋养性灵、提升情趣而投入的,物质化的倾向较少。因为,如果不是硬笔书法的名家,一位硬笔书法的擅长者,仍然是没有获得物质利益的市场的。在一种审美自由的心境下接受书法美的引导,这是许多作者乐意为之的。比起其他艺术门类,硬笔书法的创作是物质材料最少的,一支笔、一张纸即可,所占物质环境也是最小的,一张桌一张椅子即可为之。因此,它的休闲特征也很明显,随意写来,涂涂抹抹。在更大的场合卜,人们以硬笔书法交流为主,无法离开书法的社会交流渠道。这个越加宽松的文化环境为硬笔书法留出了发展的空间。
硬笔书法在自己的发展空间里建立了自己的组织、领袖人物以及审评标准。在二十余年的发展中,没有哪一种风格可以左右书坛方向,同样,也没有哪一位硬笔书法名家成为如古代社会那种入神人圣的崇高境界。这当然是社会的变迁,使个人英雄观成了集体的、社会性的化解——专家多了,风格多了,标新立异的不再是某一个人、某一家之作。社会的宽拓使每一个人都有了表现自己的机会,独立地思索、表现,对他人的宽容、理解。这种自觉来源于生活的积累、对现实艺术生活的理解,同时也获得人的自我省思和自我确认,和谐地调节人在创作中与外物、与环境生态等方面的种种矛盾。如果硬笔书法的天地日益广阔,可以断言,硬笔书法的发展将更富有生机,而硬笔书法家的积极性,包括才华、激情更易于得到张扬。
人不能离开特定的环境。人和环境有一种不可分割的性质,如果孤立地谈书法家,不涉及环境,在学术上这就是一个伪命题。譬如一个要素脱离了结构,就失去了结构的性质。因此,书法家不能脱离现有的环境,他们所具有的审美、评判以及内心的压抑、对立,都要放在这个环境下来看。毋庸讳言,由于毛笔书法的存在,对于硬笔书法的认识,还是存在着轻视、贬抑这种心理的。不论从精神角度还是物质角度来认识,都有这种忽略的倾向。尽管有专家论述硬笔书法的起源与毛笔书法等同,甚至更早,但是这种论述并不能改变人们意识深处的沉积,扭转意识深处的偏颇。硬笔书法下毛笔书法一等,在认识的累积里,已经根深蒂固无法转捩。这种观点造成的隔阂不仅是心理上的,还是实践上的。硬笔书法家中兼擅毛笔书法且有高水准的不多,交流在毛笔书法与硬笔书法领域并不具备,即便是开放意识比过去更自由伸展的今日,毛笔书法与硬笔书法还是相隔着心理上的障碍。这些都是或明或暗地存在着。可以说,硬笔书法要毫无障碍地成为生活概念和生活方式,自然而然地被大家接受的一部分,如果真的做到了,无疑成为精神提升最扎实和简便的基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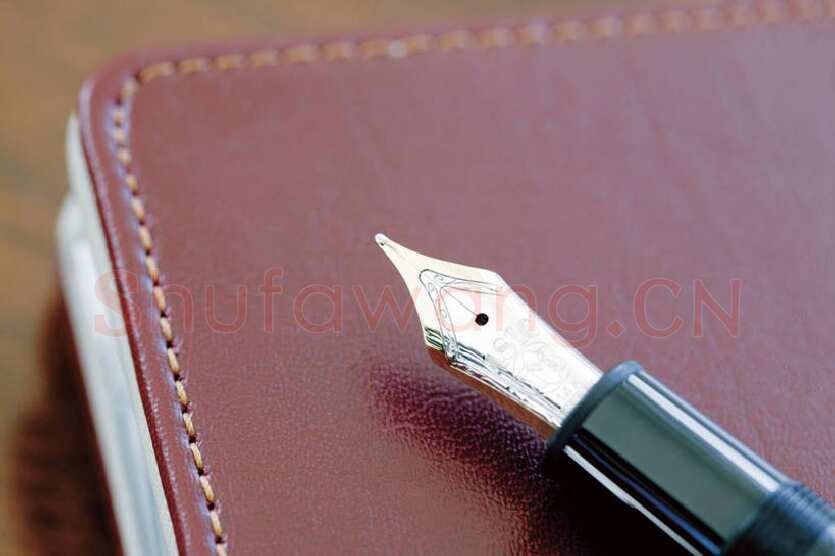
环境的利弊是相辅相成的。毛笔书法由于它在表面上的缓慢,与这个社会距离较远,所受到的冲击也更大。毛笔书法的人口要远远低于硬笔书法,并且逐渐退出转向的人多了起来。硬笔书法的人口则相对稳定些,它与这个社会的冲突力度要小得多,甚至它的实践效果,并没有萎缩而在扩大。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关注人的日常生活的文化实践里,其中就有大众文化,硬笔书法在大众文化里,并没有被排斥、抵消它的遣兴作用,还对兴趣硬笔书法的人提供一种十分简便的条件——一支笔、一张纸、一本帖,便有望成为爱好者、书法家。同时,像毛笔书法那样,形成某种压倒的习气,书风不正、不良引导,形成了丑陋,因袭的弊病,并未在硬笔书坛上形成。由于书法环境侧重于毛笔书法,使毛笔书法家对现实社会保持更多的界外感和情绪感受,诸如追风、附势、造星现象也更严重,安于研究、探讨的人少,书法家的明星化趋势日盛。这对于个人的创作心理来说,损害是很大的,至少在一个阶段里难以调整过来。这种坏现象,硬笔书坛应该薄弱很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思路,即便多有崇拜者,也不至于毫无保留地追随紧跟。硬笔书法作者基本上是走在一条效仿优秀,力求书写美观大方的道路上的。硬笔书法在仿效上尽管更多地是向时人学习,但在一些有识见的硬笔书法家里,已经有意地学习古人书法,在硬笔书法学习的同时,汲取毛笔书法的技巧和内蕴,不仅在掌握了硬笔书法的同时,毛笔书法创作也大踏步地前进。这么兼收并蓄的结果,使自己的表现手法丰富、视野开阔,拓宽了书法家的创造天地。可以乐观的是,不少书法家个人的书法生态环境正在逐渐进入一个良性循环,良好的小环境的建立,至少可以达到这么一个效果一一自娱自乐,在笔墨的进程中建立起自己的精神世界。文化心理总是要随着年龄的变化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一个人有良好的自我设置的心灵环境,又能相对摒弃外部大环境的干扰,他的发展肯定是逐渐递进的。
小环境的建立,只是整个大环境里的一个小局部。古代书法家在仕途不济时,就是退而加强构建自己的心灵之巢,藉以获得解脱和安慰。但是,这仍然是不够的,如果大环境冲突、对峙,缺乏融合、协调,生存属性肯定得不到良性的守护。我们可以回顾既往的一些社会文化环境,譬如解放之后的反右环境,许多有才华卓见的文人不是噤若寒蝉,就是掉人罗网,个人再有拓展自己学术、艺术空间的意念,也在大环境的压力下化为泡影——除非,你跟着写那些违心的文字才能得以保全。再后来的十年动乱更是一种颠覆性的破坏。大环境极其恶劣.个人的艺术生存空间就处于时刻被丧失、摧毁的地步。这样的时代要产生蓬勃的艺术生机、有创意的书法生命、有新见的学术观点,都是相当艰难的。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喜爱正常的生存环境,希望在这种环境中,自我的艺术才能得到尽可能大的发挥,与此同时自我感官与精神获得畅适。荀子说:“列是随旋,日月递熠,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次生”。人是万物之灵长,对生存环境更加敏感和强调,人类的过程,就是一个适应环境并逐渐改变环境的过程。一方面,人在生存环境中获得了自然性和社会性;另一方面,异常的生存环境也使人感到了生存危机的不可避免。从文化心理来说,人当然不希望有危机的出现,更不希望危机绵延不止,因此在面临生机遭受破坏的时候,调控就出现了,人们希望借助调控,消除危机、矛盾,达到和谐。现在,我们看当代硬笔书法的大环境,并没有达到我们期待的那种和谐境界。非艺术因素进入了书法家群体、书法家内心。当代硬笔书法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现实性和实践性特征,具有很强的服务于实际的功利性目的。一些有才华的书法家、书法家组织相互间的抵触、纷争,就是一种不谐之音。这样的书法环境无论对个人、对团体都有害无益,审美空间的自由度受到制约,硬笔书法家之间相亲、互学的风气受到破坏。在硬笔书法处在实始阶段,书法家及群体在积极地进行着理性地拓展和感性的张扬,艺术成分成了最主要的成分,使这一阶段的实践活动成为审美活动。而到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些世俗的成分进入审美活动中,削弱了书法进程中的力量,甚至把宝贵的精力耗在无谓的争纷上。当代书法行为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整体上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控制,艺术不再为某一种政治权力服务.回归书法家的心灵;但是,艺术又迅速地落满了市场的因素。市场因素一个很大的标志就是人气的归向,书法权威的树立,就是人气的相对集中。可是,艺术最终还是应该由艺术品,艺术质量来说话的。在书法环境无法形成良性进展时,艺术质量就被忽视了,而渲染、炒作、包装造成的华而不实,影响了人们的判断能力,助长了无视艺术锤炼的风气。如果书法环境不具备一种超越感,只满足于现状的名气、地位,硬笔书法的格局只会越变越小,书法家的眼光越来越短,书法家的胸襟越来越窄。可见,各种无谓的纷争如果没有止息,对书法家的精神破坏日深一日。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其模式是和谐文化。老子在分析初生婴儿的生命力极旺盛的原因时说——“和之至也”。一个书法家、一个书法团体,在初始阶段,更多的精力会投放在开拓创造之上,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良好状态。但是,持守的不易,源于来自各方面的干扰、杂念,逐渐加强而破坏着这种状态。况且,硬笔书法艺术自身的不足——系统的构建,理论的厚度、书家的素养,对于抵御不谐仍缺乏力量,很难不淹没在世俗的海洋里。这也使我们看到了和谐环境的重要,和,肯定是在万物衍生机制这个意义上派生的。《周易》称:“保台大和,乃利员”,《中庸》称:“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都很早就看到了和谐环境对于人的生息、发展的重要。现在,我们在进行人文科学探索和艺术创造的同时,应该要求人的本质力量的真诚无伪及完全地投入。从宏观上讲,我们承认分化的现实,但追求由分化走向更高的整合这么一种境界;从微观上讲,书法家必须重视从他律走向自律的辩证和谐,更多地考察自身的现状和发展,逐渐达到理想的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