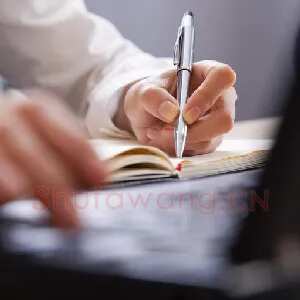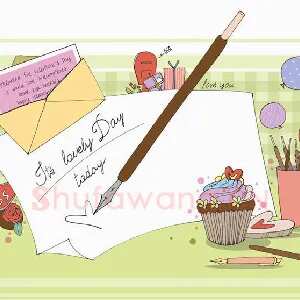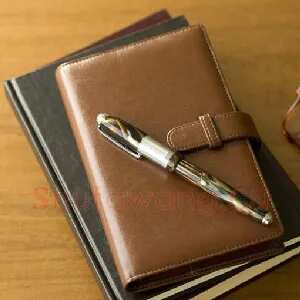名称:硬笔情结难解难舍——兼谈艺术品与市场
书法家:郦一平
分类:硬笔文摘
年代:当代
出处:中国钢笔书法
备注说明:硬笔书法文献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的高甬春兄到我公司小坐,谈及电脑网上刊登了我的一幅作品(据称还放在首页),井有一篇关于我的专访等。去附近网吧一查,果然如此。我对上网可谓一窍不通,除了感到新奇,心头油然生出许多温暖,还伴着深深的感动,正如小高所说:“郦老师,硬笔书界的同仁并没有忘记您啊!”
说来惭愧,近几年因忙于这家广告公司的事务,我如一位前数年颇为走红的歌星忽然告别舞台一般,近乎销声匿迹了。由于忙于业务,伴着沉重的心理负担,使我难免落入烦躁不安的境地,而这恰恰是浸淫艺术的人之大忌。疏于动笔,不仅只能吃老本,而且会渐渐远离这方曾经深爱过的热土。而偶尔动笔,则又会书作生疏,线条草率,这就更引来我的诸多不安,重重矛盾。尽管如此,我依然在晚间利用大量时间阅读书刊,尤其《中国钢笔书法》杂志是每期必读。使我深为感慨的是,硬笔书界近年来涌现了大批高手,且作品的质量日益提高,可以说,创新意识远比我们这些“老手”强,风格也更趋多样化。尤其看到数年前曾与之切磋过一二的高甬春、潘峰、萧望明、曾如影等已卓有成果,频频亮相专业报刊,可见几位非常努力,我为他们感到由衷的高兴,也为整个硬笔书坛的不断奋进而倍增信心。
毋庸置疑,硬笔书法已开始走向成熟,成为艺术概念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作为一个曾伴随着这门艺术成长近20年的我来说,对硬笔书法的感情可谓深矣。偶尔翻翻80年代初《中国钢笔书法》创刊号中自己那稚嫩的作品,比起近年来涌现的大批新秀之作,真感到汗颜。可以说,他们远远超过了我当时的水准,由此可见,硬笔书法确实跨上了一个较大的台阶。我想,假如没有倡导者与组织者们的努力,没有这门艺术的巨大吸引力,没有一大批硬笔书法的热衷者,达到今天这种成就是不可想象的。《中国钢笔书法》杂志的变迁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从十数年前的季刊,到后来的双月刊,发展至现在的月刊,可见作者群与读者群在高速增长。再从刊物的质量看,无论书作文章,版式设计,都与当初不可同日而语。一门艺术是否发展,时间是最好的检验标准。我记不住浩如星云的流行歌曲,更谈不上能唱会哼,而事实上这些流行歌曲也确如流星,稍纵即逝。但《洪湖水、浪打浪》、《边疆的泉水清又纯》等等老歌,却百听不厌,只要音乐声起,内心依旧激动不已,这就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艺术。我深信这类歌曲的生命力仍将延长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硬笔书法到了今天已走过近二十个春秋,可以断言,其生命力会如毛笔书法一样,漫长,悠远。因为这门艺术已逐渐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所喜爱,甚至不少人投身其中而成为佼佼者。同任何艺术门类一样,成名成家毕竟只是少数人的事情,但关键要看这门艺术所拥有的欣赏者多少,我们这些创作者为其赋予的魅力如何,是否能永久地让这门艺术焕发出绚丽的光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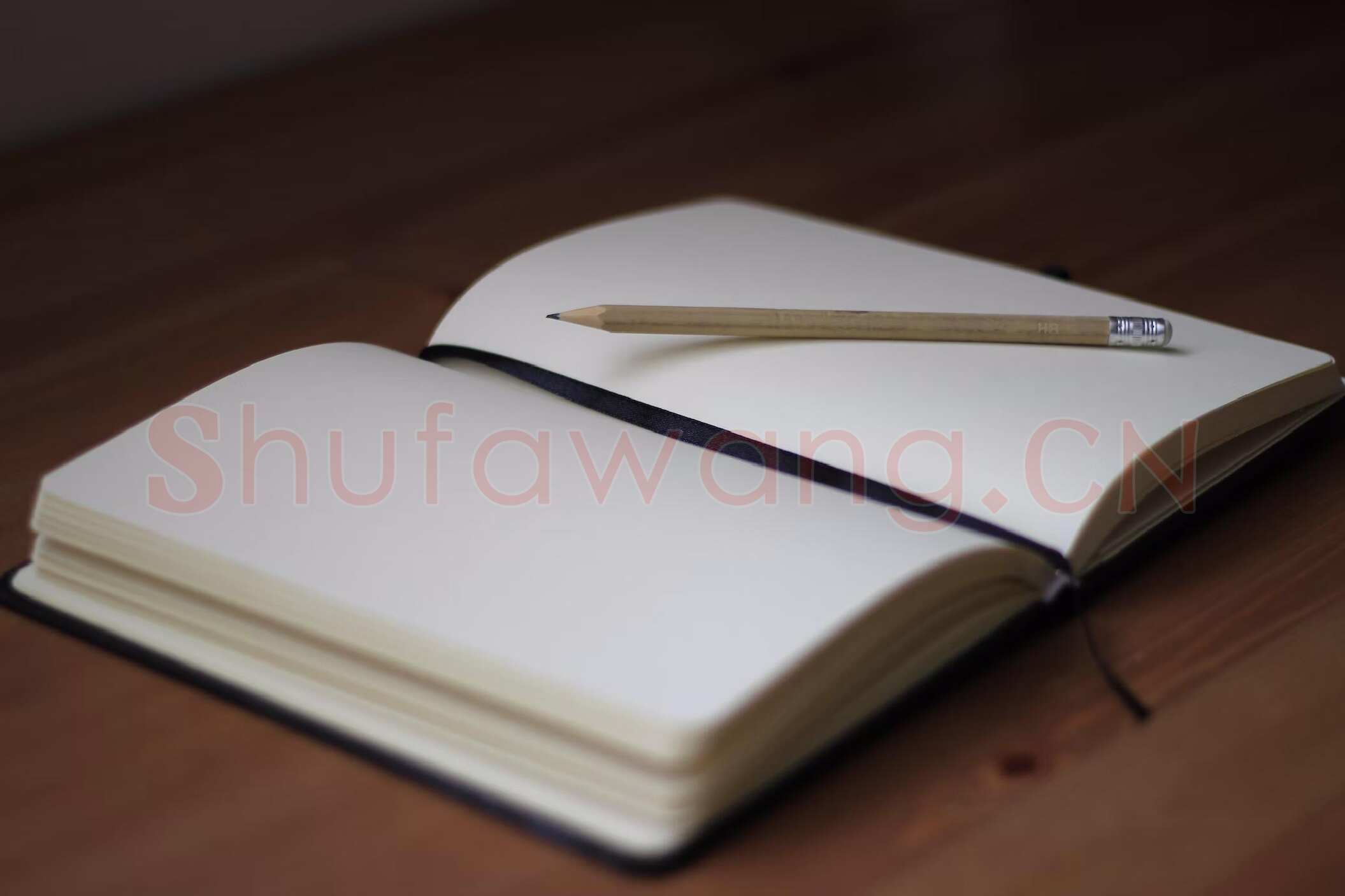
就我对硬笔书法现状的了解,以为硬笔书法走向市场是个十分薄弱的环节,亟待引起高度重视。任何一门艺术,如果只局限在自身范围内,惟有创作者与部份读者当作阳春白雪去欣赏与品味,那末,即便是珍宝也将日渐失去原有的光芒。所谓走向市场,并不是简单地用作品换取金钱,而是通过多方运作,尤其是增加宣传力度,不断使其走向千家万户,让更多的人来欣赏她、热爱她、珍藏她。然而目前的状况是不尽如意的,我们大力推崇硬笔书法如何高雅,如何具有艺术品位,但获得的效果并不理想,受到的珍视程度远不够高。我自己同样遭遇此类不幸,很多人都知道我的硬笔书法曾多次获过高奖,也发表过不少作品,有人甚至断言我的硬笔书法比毛笔书法写得更好,遗憾的是他们宁肯求我的毛笔作品或是我并不怎样的画,甚至不惜掏腰包来买,却压根儿不提起我的硬笔书作,你说是否有点惨?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说到底,在大多数人的眼中,硬笔书法地位还不高,不能与中国画和毛笔书法相提并论,也就缺乏收藏价值。这是一个不容乐观的事实,我们的新闻媒介,我们的艺术品经纪人尚没有真正下功夫为硬笔书法树立起品牌形象:尚没有为其进人千家万户而出谋划策、铺平道路。为什么会议室、大厅中、居室内可以悬挂油画、中国画、毛笔书法作品,而不能挂点硬笔书法作品呢?即便够不上巨幅标准,做一些小品不也很富有观赏性么?这个领域如果不去开拓,单纯依靠出些字帖,搞几次大展赛,办几份报刊还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有一天当我逛杭州南山路时,发现大部分画店都在经销硬笔书法作品:或居然有很多人向我索要硬笔作品时,我想这一现象肯定已得到巨大改观了。尽管我深信迟早会有这一天,但照这样等下去当然是不知何年何月了,所以我们得努力去开拓这一潜在市场,“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是毛主席说的,用在这里虽不十分妥贴,意义却很深刻。该由谁来挑起这付重担呢?我以为除了硬笔书法家自己,很难依赖其他人,因为局外人不一定喜好这门艺术,他们当然不会将时间浪费在与己无关的事情上。尤其经纪人,也即是艺术品商人,他们只会热衷去捣鼓那些能卖好价钱的艺术作品,就象服装市场的摊主,什么品牌的服装好卖就经销什么品牌,他们不会去关心销路不佳的服装。
著名品牌从何而来,当然是自身的质量与广告宣传效应两者之结合,只有让顾客了解这一品牌的知名度与优良品质,他们才会爽快地掏出腰包来。由此可见,硬笔书法除了不断提高自身的艺术品质外,尚需花大力气来树立品牌形象,不然,缺乏市场或仅仅是狭小的市场都将严重地制抑其发展与壮大。对此,我们的报刊、我们这些作者除了精心去栽培硬笔书法这棵“果树”的本身之外,是否应该花同样的精力将优质“果实”推向广阔的市场,让其拥有更多的“消费者”。
我向来不喜欢经商,印象中的商人即是刁钻势利的代名词,可如今却偏偏做起商人来,尽管别人的眼中我多少还算个儒商,毕竟搞广告带上些艺术含量和学问。与“下海”三年前相比,我的创作条件可以说大大降级了,那时期原单位领导为了保护和培养我这个所谓的人才,不惜专门辟一问供我挥洒笔墨的办公室,书籍与纸笔颜料统统归公家报销,连每次去外地领奖或参加书法活动都作为公差。而如今被人呼之为“郦总”的我却无福再拥有此等条件,我的创作大台子变成了洽谈业务办公桌,一天中大部分时间不再在宣纸上驰骋疆场,而是耗在与客户的谈质论价中。迟迟下班回家,书房内原先同样供我挥笔的大书桌早被读初中的儿子所“侵占”,无奈何只能待儿子收拾残局后再“父承子位”,却不料时间已过十点了。说实在,经商几年,也许我天生不是块赚钱的料,个人帐务谈不上有何突破,却悟出了一些艺术品与市场关系的道理,尽管艺术品不同于“娃哈哈”、“脑白金”这类商品,在营销策划与运作上却大有相通之处,优质产品需要广泛深入的广告宣传,要有市场的追捧,否则“养在深闺无人识”,结局就不容乐观了。我谈这些并不是让硬笔书法成为金钱的奴隶,而是期望通过市场的参与来进一步提高其品位与认知度,使这门经过多少有志之士呕心沥血从而成长起来的艺术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如同油画、中国画、毛笔书法一样屹立在艺术之林。
写这篇文章有点东拉西扯,既非“论”也非“叙”,完全是由感而发。也许是高甬春与我谈了一席他对硬笔书法的高见有关,所以勾起了我对这位曾钟爱多年的“老友”对硬书艺术的缱绻之情。也许,这份情结将永远难解亦难舍了!